转自:药事纵横
摘要:
新药研发的漫长周期使得研发过程中的风险极易被忽略。如何在新药I期临床前做好相关研究及降低风险,且看本文给出怎样的建议。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本文译自(DiscoveringandDevelopingMoleculeswithOptimalDrug-LikeProperties,Chapter1,P32-P37)
1、固体形式
对于新分子实体(NCE)的固体形式,不同的公司一般会在不同的时间点确定,同时也会采用不同的决策过程。但是根据作者的经验,在启动IND研究开始之前,确定NCE可开发的稳定固体形式能够加速制剂的研发,降低开发后期中的失败风险和意外发生。采用高通量技术,固体形式的筛选可以在4-6周之内,耗费大约2~5g原料即可完成。当考虑将某一固体形式进行临床试验时,应当考虑下列关键属性:
(a)结晶形式;
(b)不具有吸湿性(在高达90%RH的情况下,吸湿小于2%),对于口服固体制剂特别重要,对于胃肠道外给药的制剂,吸湿性要求可以放宽到5-10%;
(c)生产规模可放大,从毫克到公斤级别的放大应可以重现;
(d)晶癖可重现;
(e)腐蚀性:一些(很少)强的离子可能形成腐蚀性的盐,尤其是卤素盐。必须选择非腐蚀性的盐;
(f)水合物/溶剂化物: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下可重现;
(h)加速条件下,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稳定,在室温条件下至少能保持2年。
2、生物药剂学
在早期的药物发现阶段,应当为NCE构建良好的生物药剂学性质。在考虑选择最终的固体形式和制剂原理时,考虑生物药剂学也是十分重要。利用模型/模拟软件可以根据新化合物的结构预测其物理化学性质,同时根据溶解度、渗透性、溶出和动物的PK数据,可以预测其在人体内的吸收/暴露量。这些模拟方法,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资源,同时这些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早期发现问题。
除了建模工具外,简单的计算(如MAD,最大吸收剂量,Maximumabsorbabledose)也可以帮助评估人体口服吸收差的药物不良风险。在MAD的等式中,考虑渗透性(并将之转换为吸收速率常数)、溶解度(尤其是在生物相关介质中的溶解度,例如模拟胃肠液中1h,37℃)、GI停留时间(人体内270min)和胃肠道体积(250ml)。MAD模型原本是用于预测人体口服吸收限度,也可用于不同的动物种属。根据不同动物种属的生理特点,确定GI滞留时间和GI体积。
表1中列出了不同动物的的相关参数。Burton和其他MAD的参考文献采用大约270min作为典型的药物吸收窗口,研究中Tmax的时间大多数是在2~3h内。
MAD:人体最大吸收剂量(mg药物/Kg人体重)(注意对于计算动物种属,用动物的体重(kg)除以计算获得的MAD(mg/kg))
Ka:吸收速率常数(中等到高渗透化合物的值是0.05);
S:溶解度(动态溶解度与吸收更有相关性);
SIWV:小肠体积;
SITT:小肠滞留时间。
表1不同种属计算最大吸收剂量的生理学参数
对于不同化合物溶解度的函数,非临床评价中的动物种属和人的最大吸收剂量见表2。
表2非临床评价中的动物种属和人的最大吸收剂量(mg)
3、制剂原则
在选择临床试验制剂之前,已经探索了许多制剂方法,用于毒理试验制剂的开发,尤其是对于难溶性的NCE。然而,非临床的毒理试验给药剂量非常高,这取决于临床的SAD/MAD剂量。应当提前确定采用何种制剂原理用于临床试验。
一个简单的方式是根据药理剂量下NCE的溶液和混悬液的药代动力学比较作为选择临床制剂的指导工具(表3)。
表3利用药理剂量下的NCE溶液和混悬液的生物利用度对比选择临床处方
推荐临床制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新分子实体是被开发成“fisrt-in-class”还是被开发成“best-in-class”。对于目标是“first-in-class”的目标或适应症,更为重要的是尽快在非临床种属和人上验证生物学靶点,因此,推荐不会限制体内暴露量/生物利用度的制剂。这种情况下,一般选择较为简单的给药形式,例如最为典型剂型是装在瓶中的粉末、胶囊。这些剂型易于开发,可以使得新分子进入临床。然而,对于期望开发为“best-in-class”的新分子实体,靶点已经被验证,从非临床到临床的种属的给药剂量,已经被充分的理解和认知,可以用体外/体内数据预测人体内的有效剂量。因此,根据作者的经验,对于开发为“best-in-class”的新分子实体,推荐I期临床开发较为稳定的制剂并最终可以被开发成商业化产品。
4、风险及控制计划
开发评价组需要为可开发的固体形式和制剂策略提供明确的建议,此外,也需要负责识别NCE的开发风险,以及确定必要的措施减小这些风险。根据作者的经验,应当建立一个由项目关键贡献者(技术开发团队、DMPK/安全小组等)组成的交叉功能团队,进行风险识别和制定风控计划。全面的风险评估对研究团队项目支撑和优化能够提供非常有用的指导。
制药工业界有关药物发现和开发的管线数据表明,70%的NCE终止是因为安全问题,20%由于有效性,5%由于不良的药代动力学,5%由于生物药剂学/制剂原理。由于生物靶点的复杂性,或靶点本身的副作用,通过其他支持技术很能克服这些副作用相关的问题。如果一个公司选择一个高风险的化合物进行开发,尤其是这种风险来自于安全性、有效性和不良的人体内生物药剂学性能,应当三思而后行。对于任何一个“first-in-class”靶点/分子,来自于靶点验证方面的风险非常高,商业化成功的风险也非常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可开发评价组而言,及时地向研究团队进行风险反馈十分重要,以便研究团队可以转向新的分子结构,或者探索同类适应症的新靶点。当然,这应当是团队的决策。与其进一步浪费资源和时间,将研究方向转移到更有希望的先导化合物和靶点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反馈机制很有帮助,因为团队越早终止一个分子或者项目,越利于公司接受新的挑战(能够更好地利用公司内部和部门内部的资源)。尽管在上文中提到了选择高风险候选化合物的缺点,但必须承认,对于任何公司而言,追求创新,开发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增加病人的生命价值,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是必要的。
可以运用许多方法,减小NCE开发的风险,尤其是对于,期望开发为满足的临床需求的“first-in-class”的NCE。例如,合适的动物模型,并建立稳健的PK/PD相关性,并将这种关系适用于人体。开发用于人体靶点验证需要的正确生物标记物也同样重要。有时由于特定的NCE或者某一靶点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可行,那么远离这两类靶点的开发才是明智的,但如果这些项目是绝对重要的,那么,采用两到三个有希望的候选化合物开展临床,解读药效学的同时,平行开发新的生物标记物。对于NCE,一些通常的生物药剂学风险,包括缺乏可靠的人体剂量预测方法和食物效应,尤其是对于那些治疗指数窄的分子而言更是如此。如果NCE在吸收代谢和消除形态方面显示出显著的物种差异,或者缺乏适当的动物模型来显示PK/PD/效果的关系,很难预测出有效人体剂量。因此对于技术开发部门,很难开发出稳健的处方,对于早期临床试验而言,难以确定给药策略。在这些情况下,推荐采用简单的处方快速的进入临床,例如,瓶装粉末、溶液等,快速决定分子命运,而不是花费数年时间解决上面的提到的问题。对于口服给药的NCE,如果具有窄治疗指数,食物效应将造成显著的开发障碍。选择恰当的化合物,或者制剂技术,减小食物对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的影响是明智的决策,从而避免在商业化产品上出现任何可能的黑框警告。如果早期临床前体外和体内评价显示可能存在食物效应,建议在临床I期预测有效给药剂量时研究进食/禁食的影响。
最后,与固体形式相关的风险应当重视,例如没有进行多晶型研究,或者相关研究粗略,应当及时的制定相应的风控计划。例如,最终的晶型形式应当在关键临床试验前确定,应在桥接临床PK试验中评估其对暴露量的影响。分子的不良物理化学性质,例如密度、粒径、形状、流动性和可压性等,对于药物生产工艺的放大和重复性会带来显著挑战。对于风险的细致分析,并确认相应的风控计划,是开发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译后记:
在新药开发的初期,即I期临床之前,制剂开发往往不是关注的重点。
对于IND申报的审评,关注的重点是在于安全性。安全性的保证在于非临床的毒理评价,其往往与分子本身和杂质相关。而对于制剂而言,其基本开发目标往往仅在于提供一种方便的给药形式,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满足临床给药周期,能够实现的一定的生物利用度。无论是从审评机构的监管角度,还是新药制剂研发者的经验之谈而言,似乎都认为I期临床应该采用简单处方,实现临床的快速推进,从而对处方工艺的稳定性、可放大性、可商业化性并不苛求。这造成的后果往往是I期临床制剂的处方和工艺,甚至合成工艺,都难以满足商业化需求,在研发后期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工作,但是这些工作也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而由于创新药的漫长研发周期,急功近利却使得变更研究的成本、时间和风险,在前期的申报IND研究中被忽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虽然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十分漫长,快速推进的迫切压力却一点都不会比仿制药研发来得少。短暂的专利保护期,同靶点、同适应症的对手,无疑对研发者带来巨大的压力。
曾有幸听人言“制剂本身是为新分子开辟一条通往上市的道路,道路曲折轮回,如何开辟那条最短的直线之路,便是制剂人的本事”。总听到有人言,新药的制剂开发是甚是简单,确也如此,在茫茫沙漠中前行一段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译者从事新药的制剂研发亦有些时日,也一度认为新药的制剂研发过于简单。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却发现新药制剂更像是“艺术”,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却有“高下”之分。
炒股开户享福利,入金抽188元红包,100%中奖!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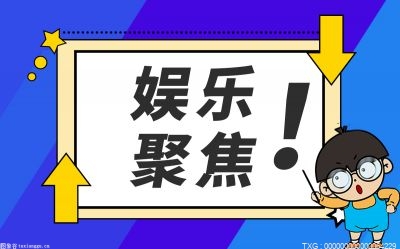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